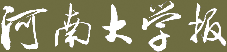雪后的阳光很清澈,像娇弱的可人儿,弱弱的,温柔的。
不管怎样,还是要说那句很多年前在《中学生作文选》里看的一句话:大地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棉花。要我说,还是当年新摘的棉花,被弹好轧在大地上;是当年新做的棉被,正暖和。
这是记忆里关于某年的某场大雪最生动的印象。
那时我靠在教学楼走廊的栏杆上,手揣在棉袄兜里,沐浴着倾斜的阳光,安静地看一群不怕冷的女生在下面空地上闹得不成样子。
下雪对我来说一直是个美丽的词,而非热闹的。因为从小到大,玩雪都非我的爱好。这点小性格来源于小时候老人讲的小故事。孩子大都调皮,一见下雪就都兴奋得不得了,在雪地里疯来疯去,身上沾的都是,手里也实实在在地抱着一大团。小手肉嫩呀,老人们心疼了,吓唬说,这雪呀看着白花花的,里面可有小虫哩,在雪里冻得不得了,见你抓着雪就往你手心里钻,可厉害了。等太阳一出来天一暖和,它们可就想出来了,就在你们手心里钻啊钻,你们这些小嫩手可就痒得不行啦。
小时候想象力太丰富,听到这些话大脑里反应出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小虫子从雪里一动一动地往我手心钻。顿时浑身一抖,立马扔了雪团,不停地揉手心,像要把已经钻进去的虫子揉死似的,又好像手心已经隐隐在痒了。
虽然没过几年就知道手痒并非是什么小虫子作怪,而是因为小手冻了,但是还是对雪有些不可名状而又无法磨灭的想法。于是这么多年来,恐惧即使没有了,习惯还是保留着。
想起傻乎乎的小时候,嘴角不觉多了一抹笑。阳光很是清淡。手在兜里捂得发热。
她们在下面玩得很猖狂,胡乱捏个雪球不分敌我地乱砸,头偏着,眼睛闭着,张嘴笑着。
现在回想当时,发觉那是一幅很美的画面:红通通的镶着白边的砖墙,大片的生动的嬉闹的人,乱飞的闪着光的雪球,叫好的助威者红通通的鼻尖,被这混乱搅起的飞扬的雪沫。而上面,是安静站着微笑的我,沐浴天光,俯视她们一如神祗。
这是一副如此美好的画面,而当年的我在写的时候,只想到一句话:热闹是她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真是傻透了。
信阳的雪不总是那么大的,经常是雨夹雪,让人讨厌。飘在天上是雪,下到地面成雨,湿兮兮的,见不着一点瑞雪丰年的样子。于是我总期盼见到北方浓密而沉重的大雪,厚厚的,踏进去没过膝盖。雪停后如大雨倾注的阳光,照在一望无际茫茫雪原上,如天女撒下碎金。虽然这只是我的想象,虽然现在我身在并不比信阳北多少的地方,但是,毕竟是有点盼头的不是吗?见过了河大雪景图,是我想象中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样子。
北海道的雪应该是很漂亮的吧?记得小时候看电视,车窗外覆雪的公路,遍布车辙,再往前,是茫茫的雪原。车缓缓地行进,透过车窗玻璃,雪世界一片浅浅的暗蓝色。从此便记住北海道这个美丽的名字。与想象中北海道的细腻不同,东北的雪,在我的概念里一直是最为壮观的。气势恢宏的暴雪暂且不说,光是小兴安岭的苍茫林海层层叠叠摞着雪的景象,就已经让人叹服了,再衬上冰雕折射的华美灯光,不知道能美成什么样子。
我一直想象着全世界的雪都落在我心里。美丽的。安静的。
觉得雪是有心情有表情的。纷乱的咆哮的,鞭打能触及的一切,乱发脾气,生气的表情。或者安静的温婉的,一片宁静雪夜,罩了零星几个茅草屋,柔顺的表情。有表情就有了色彩,没有美的或丑的,是个颜色,就能在天空下张扬。
看着天上飘下的雪花,不知怎么脑子里就跳出了一句:此曲只应天上有。很不搭,于是想起纳兰说过:不是人间富贵花。